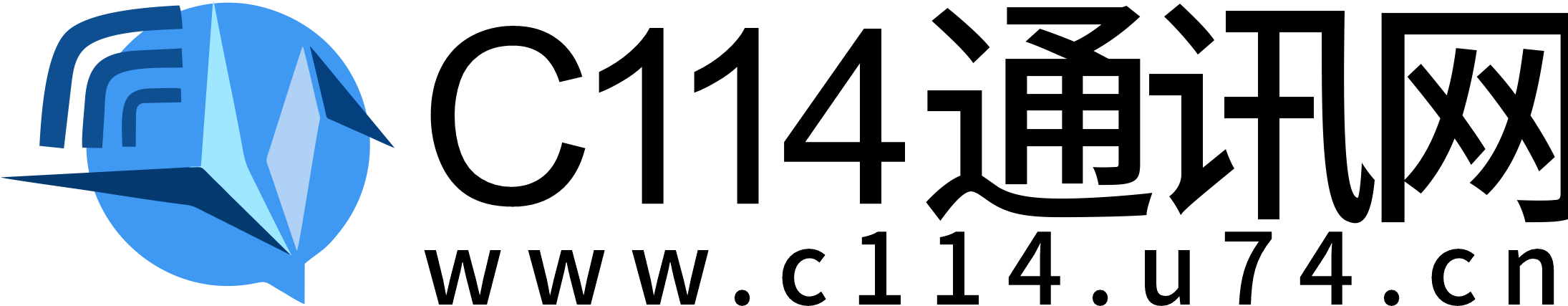来的那人拎着一盏铜制提灯,那提灯的灯光虽说不上有多亮,但是风铃花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她印有橙红色斑点的百褶长裙。
 (资料图)
(资料图)
“小姐,你为什么躺地上啊?”那人问。
这还用问?风铃花无力地指了指那块该死的石头。
“唔... ...看起来挺严重的样子... ...大小姐也没来... ...”她吃力地缓慢搬开了长久压在风铃花腿上的石头。
“总之,先把你领到我的居所去,到哪里之后,才会有办法。”她想了想,又说:“你还能走路吧?”
“左腿已经没感觉了... ...”风铃花绝望地说。
“那还是我背你。”那人就一直背着风铃花,行走在险阻的山林间。尽管她背得很吃力,走十步停几步,但风铃花感觉到了有一股强大的信念在支持着她完成这个决定,这在1899年,实在是不同寻常的。
林间清凉的风吹过两人的发梢,那人的长靴在泥水中发出清脆的声响。远处,一个头戴高顶礼帽,系着靛蓝色发带的白发人影,正在仰望着包围四周的起伏群山。她衣服上的花露水气息,被枫糖浆冲淡了几分。
风铃花被轻轻安置到了一张不怎么舒服的硬板床上。烛台上,蜡烛的数量添多了一根。
远还没等风铃花自己开口,背她的那人就已经开始自我介绍了起来:“我叫点彩,是这片枫树林的护林员。”
屋外的那人也缓步走了过来,关切地看向风铃花,仿照着前位的模板,说:“我叫十四行诗·缀折,是大英帝国诗学写作会、及植物学报告会的会员,你叫我14或者小折都可以。”随后伸出了友善的手。
风铃花并没有回应:“我可以叫你大小姐吗?”
缀折的眼神瞬时毫无光彩,冷冷地答道:“我早就不是什么大小姐了。”
点彩对缀折说:“大小姐,这人的腿伤你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搞不好是要整个截掉的,到时候她就只能依靠单拐了。”
缀折俯身下来,仔细地观察着风铃花腿上的伤口,自信且坚定地答道:“依我看来,这里面的骨头没错位,只需要简单消毒包扎,静卧几天就好——但前提是,得撒点东西。”
“烧烤料?”
缀折微笑了一下,但就只是一下:“怎么可能会?这是我离开宫廷区时,特地跑去偷的一小罐消炎药。根据我的研究,这玩意确实可行,但就是可要忍住痛了。”
风铃花实在忍不住了:“你说话都那么没感情的吗... ...14?”
“性格使然。讲话的时候我一贯保持着理性的色彩:只需要把信息准确无误地传递给别人就行了,至于感情的部分,只要你是一个社会能力正常的人,就应该能从文字中轻松地分析出来。你这个人还挺有趣的,救你是我的荣幸。”边说边用指尖转着礼帽,双眼定格在床旁斑驳的墙板上。
“啊?”风铃花被这满屏的信息填塞得不知所措。
“大小姐可真会说话,一句我的功劳都没有。”点彩末了才插上一句,话语在山谷内断续地往返,消失在幽静的夜色里。
门还没关,烛火在房间内跃动、闪烁。
是团聚的感觉。
待她们二人准备各自上床入睡时,风铃花这才知道她所躺的是缀折的床。尽管缀折每天起来时都会抱怨自己睡椅子太不舒服了,但她从来就没有被赶下床过。
第二天[注1]临近日出时,风铃花感觉到了她的伤口传来阵阵疼痛。
天还只是微亮,小屋内的一切都显得模糊,山间的天空上,正绽放着火红的朝霞。
缀折从椅子上站起,目光中充满着好奇:“风铃花——不对,我怎么会知道你的名字——如果方便的话,能讲述一下你的经历吗?听点彩说,你夜里来爬山真的是异于常人。”
风铃花惊讶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做了个深呼吸,随后便开始讲述自己不知所因的身世。
缀折只是站在床边静静地听着。她并没有什么反应,只是问道:“倘若你真的是两个世纪之后的人并不小心来到了我们这个混乱的年代,很抱歉,我并不能帮你,这种事情也没人愿意帮你。”缀折看着风铃花逐渐冷却下去的眼神,凑近补充道:“除了科依卡小姐。”
窗外的天空又变得阴沉起来,很快又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大雨。大风与水雾,在附近的地域里横行。
“科依卡?”风铃花理所应当地对这个名字十分陌生。
“对。她可是远近闻名的神秘学家。现在的科学技术可帮不了你什么。”
“好原始的东西。”
“你喜欢就好。我写封信投过去,等到她醒了自然会过来调查你的。”缀折说着快步走到书桌前,抽出一张写诗用的稿纸,用玻璃笔在纸上快速写着什么,并将信纸小心翼翼地塞进信封里,按上阴郁的蓝色封蜡。
点彩这时正准备冒着大雨照例察看枫树林的生长情况,临出门时,缀折突然抢过她的雨具,护着礼帽的蓝白色身影很快消失在雨幕与白雾之中。
“今天可真是反常啊... ...成心不让我工作是吧,大小姐?”点彩无奈地叹气着。
“竟然有这么乐于助人的大小姐... ...”
“她竟然是从宫廷区暂时驱逐出来,放到我这里进行劳动改造的。”
“啊?”风铃花轻声地叫着,起身凝视着被水珠覆盖的窗外。
到了日落时分,满是焦急的缀折终于在小屋内等到了她想要的回信:
小折:
我可不愿意为了一个残疾人跑着跑那,让她自己来(死了就算了,我不是法医)。
干嘛非得找我?
无趣地,
在此签名:Cyk
日期就是今天
睡的昏昏沉沉的风铃花艰难地掀开被子,靠在枕边,看着缀折紧张的表情:“唔... ...?”
“看起来没用。”缀折把信递给风铃花。
过了几秒后风铃花就大笑起来:“你这位神秘学家可真有个性!这就是你所说的人脉?”
缀折沉默了一会:“不。有很多人来与我交朋友的目的都是趋炎附势,求取钱财。但唯独科依卡小姐不是这样的。”
“这样吧。”缀折坏笑了一下,“我给你一点选择的空间:是现在我抬你出去还是等几天伤好了自己走路?”
“Whatever.”风铃花大脑一片空白。
“猜的真准。我这里可没有担架——只好浪费你的时间了。”
风铃花的伤,在以极快的速度恢复着。在缀折和点彩夜复一夜的精心照顾下,她几天之后就能勉强地下床走路了。她能够感受到,19世纪末整个世界的温暖好像都在向她涌来。
风铃花与缀折一起在小屋内静坐着等待点彩踏着积水护林归来。
“这么快就好了!”点彩远远地望见站着的风铃花,立即冲过来给她一个拥抱。淡蓝色和橙色的发丝交织在一起。
“要踏上回家的征程了吗?”缀折给风铃花左腿又缠上了几圈绷带,烛光,映照出了她银蓝的双色瞳孔。
近处,水雾打湿了她们的胶布雨衣,互相自言自语地寻找着通路。
远处,她们手中的提灯在浅雾缭绕的山谷中,形成了一条若隐若现,触亮新生活的光带。
[注1]:指风铃花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二天。